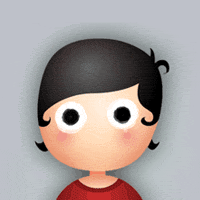谢有顺小说课堂之十:内在的经验
来源:谢有顺新浪博客
在《内在的人》一文中,我指出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不同,它深入的是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写的是人类内心那种极为隐秘而细微的经验,那种不安、恐惧、绝望,根植于内在的人——这个内在的人,是一种新的存在经验,也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主角。在这个内在的人里,作家追问存在本身,看到自己的限度,渴望实现一种存在的超越,并竭力想把自己从无能、绝望、自我沦陷的存在境遇里拯救出来。而如何才能获得救赎,这就不仅是一个文学话题,也是一个宗教话题。
谈及宗教,东西方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他在小说的最后所出示的对未来那种宗教般的希望,是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他对现实绝望,但对未来却充满着模糊的信心。在此之前,狂人对“这伙人”有一个警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①而没有吃过人的人,才是“真的人”。从“真心”到“真的人”,这里头包含着鲁迅对现实的理解。其时的鲁迅,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所谓“真的人”,显然闪烁着“超人”的影子。但“真的人”究竟是什么面貌,有着哪些内涵,鲁迅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是鲁迅借来的文化符号,既没有传统的根基,也没有宗教的想象力。尼采尽管是反的,但他提出的“超人”,明显受了《》中“新人”的启发,仍然带着某种宗教色彩。鲁迅笔下的“真的人”则要空洞得多,难以在中国文化中落地,所以,《狂人日记》里有大量不像小说语言的杂感,更像是思想笔记,鲁迅借此重在提出问题,喊出自己的声音,但狂人的这些思想如何产生、何以产生,他并没有合理地交代。读完《狂人日记》,我不禁在想:狂人是从哪里得到的善的知识,从而知道吃人是不好的?在他眼中,大家都吃人,四千年的历史,无非是写着“吃人”二字,“我”在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混了多年,也成了“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既然如此,狂人何以知道吃人是要不得的?又何以知道“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在鲁迅的精神视野里,他并不相信有一位救赎者——上帝,具体到狂人身上,也就没有一个外在的声音来提醒他该不该吃人,他的所有价值判定都来源于自我觉悟。鲁迅的生命哲学是不相信有外在救赎的,他只是对生命本身存着一种自信,他接受尼采,也和这种生命的自信不无关系。他相信生命会发生改变,这也暗合了古代圣贤的教导,只要你肯努力,人人皆可成尧舜,“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一切从心开始,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所以钱穆说中国若有宗教的话,那就是“人心教”。王阳明去世前写“我心光明”,弘一法师圆寂时写“悲欣交集”,讲述的都是心的故事,是个人的内在觉悟。觉悟即救赎,一种中国式的救赎。
但在西方的文学背景里,生命的改变或存在的救赎,主要得力于倾听外在的声音,无论是“旷野的呼告”,还是关于拯救的“福音”,都被描述为是来自上帝的声音,人只不过是这种声音的倾听者和跟随者。通过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一个人内心,并通过这个声音所传输的生命意志,来完成对生命的救赎,以“新造”代替“旧造”,以“新人”代替“旧人”。这种对生命和救赎的理解,就是宗教的角度,它并不依靠人的觉悟,而是仰赖上帝的力量来获得拯救。因此,人的有限与上帝的无限,人的堕落与上帝的圣洁,就构成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根本冲突。我们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读卡夫卡的小说,关于上帝是否存在、人如何才能获救的问题,一直他们小说里的中心问题。他们在相信与怀疑之间徘徊,但上帝存在与否可以争论,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不具备永恒的品格,所以也就无法实施自我拯救;人离开上帝之后,不断堕落,最终完全被自身那黑暗、绝望的经验所粉碎,如卡夫卡所形容的,人成了虫豸,成了小动物,只能内心惶恐地谛听外面的动静。人要从这种境遇里得救,就只能等待圣灵的降临,等待拯救者的到来。
这就是西方文学最为普遍的内在经验,它充满深渊的呼告,也时常发出拯救者到底在哪里的哀叹。文学的内在性,其实和这种呼告的精神、追问的经验密切相关。《旧约·约伯记》所写的约伯的追问,就是一个经典的主题。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击杀了它的牲畜、仆人,剥夺了他的财富、快乐,使他的家庭破败,身体长出恶疮,极其痛苦,于是约伯就哀叹,抱怨,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而是反问他:“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密处行走么。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么。死荫的门你曾见过么。地的广大你能明透么。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②最终,约伯“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出发,是很难读懂约伯的遭遇的。约伯已是一个正直而敬畏上帝的人,?中国的文化重行为和表现,约伯的好,符合现世一切道德和伦理,但在背景里,这个故事就具有奇特的内在性:约伯所受的试验并非因为约伯不好,而是约伯以自己的这个好为好,这在《》里称之为“自以为义”。以自己的义为夸耀,就否认了信仰的意义。《》强调“”,它的意思是说,你的行为、表现不能成为你的义,这就好比一个犯了死罪的人,他再做好事也不能改变他是一个罪人的事实。罪的消除不是来自于自义,而是来自于赦免;而赦免是一种权柄,它只能来自于一位无罪者,这位无罪者就是上帝本身。因此,当你自以为义的时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一种不信,这就是约伯的困境。
从宗教意义上说,不信是最大的罪。这一点,不妨来看一下伊甸园的那个故事。、夏娃说,不可吃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必定死”。但夏娃却在蛇的诱惑下,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亚当也吃了,这就意味着他们面临着死的结局。这里的“死”,不是肉身马上终结,而是指亚当、夏娃从时间之外进入到了时间之内,从此之后,死亡会拘禁他们,时间会限制他们,他们再也不是有永恒生命的人了。夏娃和亚当吃果子,看起来不过是犯了一个很干净的罪,可是这个干净的罪背后,有一个罪的根源,。不信的罪,才是人类的原罪,它比说谎、杀人的罪要大得多,因为说谎和杀人仅是一种行为,而不信是一种性质。性质的罪,大于行为的罪;行为的罪,是从性质的罪里派生出来的,没有罪的性质,就不会有罪的行为。为何说恨人就杀人,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先有了恨,行为上他才去杀人的。所以,一切罪的根源都来自于不信,因为不信,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因为不信,人类在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因为不信,人类无法从根本上获得拯救。
所有罪的思想的核心,都是指向那个不信的罪。正如所谓的罪人,不看你是否在行为上犯了罪,而是因着不信,你在性质上就已经是罪人了。是罪人,就需要悔改和救赎,就需要重新回到相信的道路上来,以重新确认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观念,和东方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按照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的看法,西方社会的文化形态和日本的文化形态,可分别归结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③罪感文化的道德标准来自宗教传统,来自上帝。李泽厚则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肯定现实、此世的价值,以身心幸福地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作为理想和目的,所以,中国人很少有罪感意识。
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品格,它必然是以书写世俗生活的幸福与残缺为主体,而少有追问存在困境与寻找精神救赎的意识。王国维所说,中国文学更多的是写民族、国家、人伦的主题,而缺少探索精神、心灵和宇宙的文学传统。前者以《桃花扇》为代表,后者以《红楼梦》为代表。《桃花扇》式的关怀现世的作品为多数,而像《红楼梦》这种贯穿着精神性、超越性母题的作品,即便是到今天,也还是不多见的。《红楼梦》虽然也写实,多表达日常人情之美,但它以实写虚,创造了一个精神的幻境,在价值观上,它是有天问精神的。这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是一种珍贵的叙事资源。
事实上,一部作品中是否有精神追问,是否有存在意义上的呼告,它的境界是大不相同的。这令我想起一个学者在一篇文章中说,由于自己早年读过了太多伟大的俄罗斯小说,所以现在根本无法阅读中国小说。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感受。俄罗斯文学里面所响彻的,都是非常宏伟的精神辩论,托尔斯泰等人所写的,完全是一种内在的经验,他们绝不会把笔墨停留在那些无关痛痒的事上。鲁迅论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有一个精准的概括:“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④确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审问者和犯人是同时存在的,这就为作品创造了一个自我辩论的场域。一个我在审判另一个我,一个我又在为另一个我辩护,这种争辩,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精神旋律。鲁迅的深刻,也得益于此。他的作品,往往也具有审问者和犯人这两种精神维度。他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是审判中国的历史,审判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兄弟、母亲,也都是吃人的人;另一个方面,他也不避讳我也是吃了人的人,认为妹妹死的时候,他们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地给我吃。鲁迅在杂文里也多次说到,吃人的时候,我也帮助排这个吃人的筵席,我也是吃人者当中的一个。如果鲁迅仅仅是一个审判者,批判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那他就不算深刻。他把自己也摆进去,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这种写法,在中国传统中是罕见的。鲁迅说,我不单是无情地解剖别人,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在给许广平和其他朋友的信中,曾反复强调,自己的思想过于黑暗,觉得身后仿佛有鬼跟着,总是拖着长长的黑影。他看到了自己灵魂里的残疾、黑暗和肮脏的,但他不回避这些,他正视自我内部的疾患,这是了不起的一种眼界。
只是,鲁迅之后,有这种自我审判意识的作家太少了。在当代,有太多的作家都在写那种醉生梦死、欲望横流的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读不到一丝作家的自责,更没有自我审判、自我愧疚的姿态。其实,忏悔、自责是特别值得珍视的写作情怀,它能够把一个人的写作,带到另一个境界。譬如,我曾经听莫言在几个场合说过,包括他谈自己的长篇小说《蛙》,反复说要把自己当作罪人来写,这对中国作家而言,显然是一个新的写作角度。因为莫言一旦有了罪人及罪感意识,他的作品就会打开另一个精神空间,就会诞生新的内在经验。
余华的写作也是一个例证。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用非常冷静的口吻写下了像《现实一种》或《一九八六年》这些作品,那时有人读了作品后说,余华的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其实,那时的余华,在冷静的叙述中,对人性一直有清醒的批判和揭露,也暗含着一种隐忍的爱。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出色地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那个内心充满恐惧和颤栗的孩子,就是一个“内在的人”的形象,而因着有这种内在经验的书写,这部小说也就获得了独有的精神深度。小说里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一个孩子因为在背后嘲弄老师,说他怕老婆,只要他的老婆来了,。老师知道后,说要惩罚他,那个小孩就整节课都充满恐惧,等着老师的惩罚降临。后来发现,老师下课就走人了,他以为老师忘记惩罚了,他的恐惧也就随之消失。可是,恐惧刚消失不久,老师又出现在了他面前,说我还没有惩罚你呢。孩子的心情一下子又落到了谷底,他又一次回到了那种即将要接受惩罚的恐惧中。反反复复,那个孩子就这样被折磨了好长一段时间。通过不断地延迟惩罚的来临,余华把一个小孩内心的恐惧,写得真实、动人。这些都构成了余华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内在经验。
但《活着》之后,余华的写作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活着》对人之命运的书写,尽管充满悲怆,但相对《在细雨中呼喊》而言,写法上要简单得多。《活着》里人物命运的悲怆感,多半是来自于死亡事件的简单叠加——通过不断地死人,到最后,死得只剩下福贵一个人了,让你不得不觉得人生真是悲剧。《在细雨中呼喊》里那个孩子的恐惧,是有深度的、内在的,充满存在意义上的复杂感受;到《活着》里的福贵,他的苦难更多的是成了一种外在的遭遇,没有多少精神挣扎,甚至福贵面临悲惨遭遇时,前后也没有多少内心变化,他面对每个亲人离去时的感受是相似的。。福贵的悲怆,在于不断地有亲人死去;许三观的痛苦,。福贵的人生中,前后死了七八个人,而许三观的人生中,一共卖了十几次血。我曾经看过一篇评论文章说,就叙事的设计而言,《活着》也可以更名为《福贵丧亲记》,它们在叙事模式上是相似的,都是通过外在遭遇在同一层面上的叠加,迫使读者觉得这个人活得真惨。这就有点像电视剧的模式了,以一个好人为主线,故意把各种苦难都压在他身上,由此来激发观众的同情心。王朔概括他们当年编电视剧《渴望》,就是按这个模式来设计的,一个好人,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难他,但最后她没有被打倒,这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长今》、《沐府风云》等电视剧,用的其实也是这种故事模式。
《活着》最后写到,福贵和一头牛对话。这里面有一种禅宗的思想,人变成牛了,具有牛一般的忍耐力和承受力了。这表明人承受了无数的苦难之后,已经麻木了,苦难也已经不再是苦难了。余华把这解释为福贵的内心变得宽广了,但也可以说,这是内心麻木了。这是很典型的中国人对待生存困境时的态度:他不会在苦难的处境里一直追问下去,而是会找到一种消解苦难的方式,使自己快乐起来。这就是刘小枫所说的“逍遥”精神。他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说,西方人在面对苦难时会选择旷野呼告,以期待拯救者的出现和来临;中国人则通常选择对苦难进行自我消解,进入一种逍遥、自在、忘我的境界,以期实现对苦难的忘却。福贵就是一个忘却了苦难的人。
如果只有逍遥哲学,文学是很难获得深刻品格的。我们读鲁迅的作品,为何会觉得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品质?就在于鲁迅不是逍遥的,鲁迅是承担的、前行的。比如在《过客》里,有这样的提问:“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老头说,前面是坟,小孩则说,前面有鲜花,有野百合、野蔷薇。这是鲁迅对人生的真实看法。他有篇文章就叫《坟》,“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可是鲁迅又对未来、对孩子存着希望,所以也会注意倾听孩子的声音。过客说:“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老翁说:“那也未必。太阳下去了,我想,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罢,像我似的。”过客说:“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老翁说:“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么?”“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过客说:“不行!我还是走的好。我息不下。”⑤——这里特别强调了有一个声音来叫我,我不能停下来,我还是要走。这其实是关于存在的一种倾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过这种声音,但对这种声音往往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像老翁一样,叫了几声我不理它,它也就不叫了;还有一种是像过客这样,无法不听从这声音的催促,要继续往前走。
我想,关于存在,关于内在的人与内在的经验,都可以用这个声音问题来总结。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自我,都有其内在的经验,以及内心的生活,无论年轻还是年老,都是如此,关键是我们听不听从内心的召唤。按鲁迅的解释,内心的声音可以来自生命本身,这就是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心里面那善的声音,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生来就有“四端”,有恻隐之心、丑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内心的声音都会出现,它告诉我们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并等待你的内心作出抉择。在西方文学里,这声音往往来自人以外,来自那个更高的拯救者,是他在召唤人,并激发人起来跟从这个声音。
说现在是向内转的时代,其实就是说现在正进入一个倾听内心声音的时代。里面的声音一旦越来越响亮,外面又有倾听和配合者,并不断地有人站出来呼吁人应该如何活着、如何有意义地活着,现状就会发生改变。
其实,鲁迅所说的审判者和犯人的辩论,也可看作是一种关于声音的较量。这种较量,往往就是一种自我辩论。内在的人,是经常有不同的声音在内心激辩的人;内在的经验,就是这种内心激辩的真实写照。德国学者G·R·豪克有一本书叫《绝望与信心》⑥,他阐释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当今时代而言,绝望的存在可能是一个无以辩驳的事实,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绝望的背后,还有微弱的信心,还有希望的存在。两种声音的辩论,绝望与信心的交织,就构成了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一种有重量的文学,就应该多关注这些内心的争辩和较量,就应该在作品中建构起这种独特的内在经验,惟有如此,文学才能有效地分享存在的话题,并为当下人类的存在境遇作证。⑦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