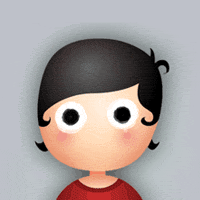《世说新语》与古代文学的精神史研究
本书的基本内容是通过《世说新语》及有关材料[i],研究魏晋时期文人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及其在中国文人精神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研究《世说新语》?精神史的涵义应当如何理解?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特征是什么?《世说新语》又如何反映了这样的精神变化?从文学史角度的精神史研究现状如何?本书的研究与他们有何差别?这些都是首先应当说明的问题。
西方语言中与汉语“精神”一词的对应词有两个,一是“mind”,指一个人所思想和感觉的东西,包括思想、精神和愿望等。它就是哲学上与“物质”(matter)相对应,与“意识”(consciousness)相一致的哲学范畴。它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和成果的总称。另一个是“spirit”,它来自拉丁文“spiritus”,意思是轻薄的空气,轻微的流动,气息。它与“肉体”(body)相对应,既指个人的心灵和精神,也指表现其心灵和精神的气质和风度状态。西方哲学界对精神现象的全面关注大约始自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处女作《精神现象学》。该书的主题是描述人类意识自身从最初的感性知识向科学发展的历程,即哲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显然,黑格尔所说的精神主要是“mind”的涵义。
中国古代典籍中“精神”一词的涵义分别与西方“mind”和“spirit”这两个词对应。《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ii]《吕氏春秋·尽数》:“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矣。”[iii]前者指的是人的意识,后者指的是区别于形骸的人的精气、元神,大致与西方“mind”一词相同。而宋玉《神女赋》中“精神恍惚,若有所喜”指的则是人的神情意态[iv]。这个意思成为后来许多文章形容人的精神状态的代表性用语。如《世说新语·言语》“周仆射”条刘孝标注引《晋纪》:“伯仁仪容宏伟,善于俛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v]指的就是周顗那神采焕发的精神状态。宋代周美成的《烛影摇红》词:“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vi]也是指人物的风采神韵。显然,后一种用法与英语中“spirit”一词比较贴近。从汉语中“精神”一词的用法来看,两种意思既又区别,又有联系。我们这里所讲的中国文人精神,主要是指这后一种用意的“精神”涵义。即指文人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采。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的说法可以首肯的话,那么以眼睛为焦点的人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就是人的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而对于这种作为人的心灵写照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更应当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英国现代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则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关于心灵的知识都是历史的”,“历史知识就是人类心灵关于它自己所能有的唯一知识”。所以他将通过心灵去认识思想,并借以达到认识历史的方法作为“认识别人的心灵或者一个团体或者一个时代的集体心灵(不管这个用语确切的意思是什么)的唯一方法”[vii]。按照这个逻辑推论,文学史显然也是一部人类的心灵史,也是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这正如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viii]这个观点之所以对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文学是人的灵魂史,是人的精神立体运动的历史。这对于将“文学是人学”简单地理解为文学作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诠释的传统社会学观点,不啻是一个本质的飞跃和超越。因为人的心灵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而文学作品又是洞悉时代灵魂的显微镜。丹纳(Hippolyto Adolphe Taine)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从这方面看来,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ix]
如果说先秦理性精神的意义在于人对自然天命意志的超越的话,那么魏晋时期文化变迁的意义就在于人对于传统社会意志的抗争和超越。这种传统是周秦以来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及反映这种制度的封建专制体制下形成的,并在两汉得到高度的强化。因此,人们才将魏晋精神比之为欧洲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胜利。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在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冲破欧洲中世纪的思想禁锢的意义时说:“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x]联想到中国汉代思想文化的禁锢沉闷局面被活跃自由的魏晋文化所取代的情况,令人感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作为魏晋时期文人精神变迁的一面镜子,《世说新语》广泛记载了魏晋时期文人的生活言行[xii]。、思想文化乃至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其中最根本的转变,就是当时士族文人在精神领域从精神面貌到精神境界的巨大变化。如果拿《晋书》、《资治通鉴》有关魏晋时期的记载和《世说新语》的内容作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五胡乱华、永嘉之乱等在《世说新语》一书中只是被作为很多故事的背景加以交代,而不是将其作为描绘的主体。宁静而美丽的山水、闲适而恬淡的心境、智慧和热情的论辩、神超而形越的人生境界,这些才是编纂者们苦心营造的人间乐土和理想之国。它那令广大文人神往不已的精神气质和音容笑貌,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特别青睐,“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xiii],就是因为它的编纂者们以其灵敏的嗅觉,不仅发现了魏晋时期文人精神境界的本质所在,因而搜集了有关的大批逸闻,而且将其提炼总结,把其中最能够体现这种时代精神和心灵脉搏的逸闻故事汇编成册,故而成为千古不朽,永远充满魅力的奇妙作品。它以故事的形态,生动地展现出那个充满变化的社会氛围中文人们精神面貌的深刻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和灵魂魅力传统,是由《世说新语》加以挖掘和系统整理,因而被历代文人会心接受的。明代胡应麟赞美该书道:“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xiv]而《世说新语》在历代人们脑海当中形成深刻印象的,也主要是那些展示魏晋文人心灵和精神的生动传神,令人回味无穷的精神写照。清初钱棻《玉剑尊闻序》云:“《世说》一书,人但见其娴婉新粲,足以鼓吹休明,而不知点染生动,能使读其书者如亲承乐、卫之韶音,躬接殷刘之玄绪;神明意用,跃跃毫端,若长康之貌裴令颊上三毛,识具顿现。非擅化工之笔者其能之乎?”[xv]大约同一时期的毛际可也说:“昔人谓读《晋书》如拙工绘图,涂饰体貌,而殷、刘、王、谢之风韵情致,皆于《世说》中呼之欲出,盖笔墨灵隽,得其神似,所谓颊上三毛者也。”[xvi]因此,《世说新语》的传播影响和接受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精神气质和灵魂魅力形成的历史;对《世说新语》的精神史研究,也是对中国文人精神气质传统的重要研究。
作为文学作品精神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文学作品本身与其所反映的对象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之间的种种联结点,更要探索那些能够作用和制约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各种社会因素:,到社会思想潮流;从宗教文化,到文学艺术;从人生观念,到风俗习惯。当然,这些探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已经硕果累累的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的研究,而是为了解开那些心灵和精神世界的神秘疑云去寻找各种有效的钥匙。因此,以心灵和气质面貌为对象的精神史的研究需要思想史等方面的帮助,但绝不等同于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
遗憾的是,尽管从精神和心灵角度研究文学的理论观点已经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但迄今为止完全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系统研究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论著还绝少见到。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学者吉川中夫先生的《六朝精神史研究》一书[xvii],该书将其“精神”的研究范围界定为“思想、宗教和学术的综合体”。说明他大体上是按照西方“mind”一词的涵义来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的。从六朝时期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界定是比较符合实际和新颖独到的。作者的工作也完全实现了自己的初衷。笔者以为,对于六朝来说,以思想、宗教和学术为主体的理性精神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作为这些理性精神派生物的人的心灵和气质的研究也同样重要。因此,我才把自己的研究范围界定在以外在面貌所反映的心灵和气质的方面,即通过魏晋文人的音容笑貌所反映的精神世界,去探索造成这种精神世界的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这样,我们的设想就是以“spirit”为研究的突破口和主要对象,进而达到从“mind”的高度对“spirit”把握。
此外,古代文学的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实践,并取得了如
(此文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年第3期)